【我的西医岁月——1972级医学校友毕业50周年纪念】医者初心五十载 杏林筑梦正当时
张引成,1972级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一、岁月淬炼:从困顿岁月到医学殿堂

1972年,当国家招收首批“工农兵学员”的消息传来时,我正以人民教师的身份站在三尺讲台,而这一纸录取通知,竟成为我人生转折的钥匙。
走进西安医学院的校门,心中满是对知识的敬畏与对党的感恩。班里同学年龄相差悬殊,从老高三到初一学子,却都怀揣着同样的热忱。课堂上,我将“党和人民的信任”刻进骨子里,别人记一遍的解剖图谱,我便临摹十遍;别人背一遍的药理公式,我便默写到深夜。至今仍记得,在油灯下啃读《生理学》课程的冬夜,窗户玻璃上的冰花与课本上的铅字同样清晰,那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医学启蒙”。
二、杏林深耕:从临床实践到科研突破

1975年毕业时,我被分配至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我在日记里写下:“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党交付的使命。” 面对颌面肿瘤、唇腭裂、外伤患者,我常常在手术台前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记得一位因车祸导致下颌骨粉碎性骨折的农民患者,术前绝望的眼神让我彻夜难眠,查阅数十本资料后,我设计出改良固定方案,术后患者握着我的手哽咽道:“张医生,我终于能好好吃饭了。”
1983年,我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班,主攻颌面外科。在研究三叉神经痛时,我偶然发现在小鼠颅内注射阿霉素可阻滞三叉神经节传导。这个灵感让我彻夜难眠,反复在动物模型上验证后,我将其应用于临床。当一位被病痛折磨十年的患者告诉我“痛感消失了”时,手术室里的灯光仿佛都在闪烁。这项研究后来发表于《中华口腔医学杂志》上,荣获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更成为国内三叉神经痛微创治疗的重要参考。
三、医者仁心:从三秦大地到全国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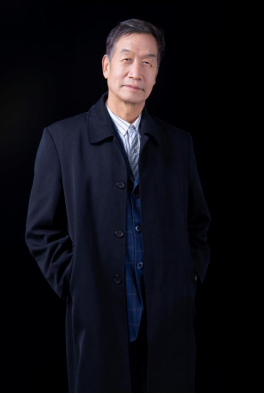
从医数十载,“以患者为中心”不是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准则。曾有甘肃患儿家长连夜驱车800公里求诊,我于凌晨三点赶到医院为孩子做唇裂修复;山东一位三叉神经痛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未果,我为其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随访五年未再复发。北京304医院曾专程发来邀请函,邀请我作为主刀施行复杂颌面肿瘤手术。我想,医者的价值从不在头衔高低,而在能否让患者重获微笑。
这些年,我从住院医师到一级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从“西安交大先进工作者”到“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头衔在变,但初心未改。记得获评“省优秀共产党员”时,老院长握着我的手说:“宗濂老院长当年为研究针刺麻醉,把自己合谷穴组织做成切片,这才是医者该有的样子。” 如今站在侯宗濂教授的塑像前,我常想起母校的教诲:医术要精,医德要正,医心要诚。
四、母校情深:五十载风雨,归来仍是少年

今年是我们毕业50周年,回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梧桐树还是当年的模样。想起我的导师胡永升院长的言传身教,郑遵畅老师生活中的谆谆教导,李同良老师讲课时的幽默,樊小力老师条理清晰的板书,想起实验室里一起做实验的同窗,宿舍里彻夜讨论的医学难题。母校不仅教会了我听诊器下的精准、手术刀下的沉稳,更教会我“医者仁心”的真谛。
如今我已两鬓斑白,但每当穿上白大褂,走进诊室,看到患者期待的眼神,仍能感受到1972年那个春天,第一次走进医学院时的澎湃心跳。五十二年党龄,五十年从医路,我愿继续以初心为灯,以仁术为剑,在杏林路上走得更远。因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党的忠诚,早已融入血脉,成为此生不渝的信仰。
2025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