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两位导师
作者:高孝先,内燃80级。曾任TCL集团常务董事,通讯股份公司董事总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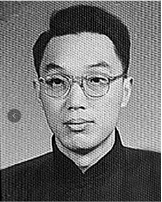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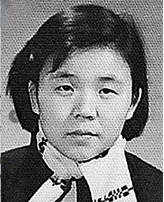
我的研究生导师宋雅莼教授昨天平静地离世,宋老师的丈夫潘宇鹏教授也已经早几年过世了。两位老师的学生们在微信群里纷纷表达了对老师的怀念与祈祷。
我们无论是在校期间,还是毕业离校一直习惯了称呼潘老师宋老师,这一点还确实有点不同,尽管他们作为资深教授也有一些社会兼职。校园里不乏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他们或是院士,或是某国际权威机构的会士,学生们完全习惯了均称“老师”。
三年读研只有一次潘老师因晚上才有空,约我到老师家里面授,这也是我在交大十年唯一的一次去老师家里,包括所有的老师。我只带了几本书籍和笔记本,倒是在我落座不久,宋老师居然端出一碗醪糟鸡蛋羹给我,当时的我只有用受宠若惊来形容。
研究生毕业之际,潘老师曾问我的打算,当时老师有意让我继续留校工作,并且大概地讲了老师们准备办一个学术刊物。无奈我当时已经心系南方,其实也有对自己从事专业研究信心不足的因素,老师并未因此而怪罪我,反而说我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助的尽管提出来。
我到惠州工作不几年,两位老师退休移居深圳。我们也因此方便来往了一些。潘老师曾担任过几年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两位老师一边忙于事务性的顾问工作,一边还在继续自己的专业研究。潘老师离世前约一年时间,腿脚已经不像往日那么灵便,思路依然活跃。一次去看望他们时,老师还拿出一沓书稿,说他的新专著写作过半。望着老师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打算,我的内心翻腾不已,老师对自己事业的热爱溢于言表,不禁令我自愧弗如,也觉得有愧老师的期望。
两位老师在生活上是典型的交大老师的形象,衣装整洁而不华贵。退休后师生相处没有了在校时的严肃,甚至令我感到老师的些许童趣。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看望老师,老师高兴地说他们要做东吃饭。并且强调他们得到了一笔不少的补贴,好像是宋老师得到了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我们特意挑选了深圳一家有名的淮扬菜馆,师生欢聚一场。结帐时当然是学生们抢着付钱,送老师回家的路上,二老不住地说,该是他们做东,怎么我们买单,我只好安慰老师说下一次我们再找一个更好更贵的餐厅让老师请客。
潘老师1952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曾任西安交通大学技术经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还担任过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和陕西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著有《辨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技术合同法讲座》、《当代科技的发展趋势》等,是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
宋老师也是1952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曾任西安交通大学法学教授、社会科学系主任。她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获得者。主要著作有《技术合同法及其实施》、《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法学》、《关于器官移植技术的法律思考》、《安乐死立法初探》、《关于产权问题的法律思考》、《无形资产评估导论》等。
两位导师还是我国技术合同法的起草者,在我国经济法研究领域有着很高的威望。80年代中期,潘老师和宋老师联合章德安、施明德等四位教授联手打造的西安交大技术经济法律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的经济法学硕士学位授予点之一,开创了全国理工类高校培养法学研究生的先河。今天的交大法学院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可谓是风生水起,桃李满园,这个局面足以告慰老师的在天之灵!
作为一个不成器的学生,唯愿两位老师安息!!
2019年10月10日